-
- 上一篇: 2017超级搞笑段子来袭 让你过年乐翻天!
- 下一篇: 幽默与笑话的版块栏目
又到了秋菜上市的季节,小区广场停着三五辆白菜车。一棵棵大白菜,油绿的叶子,雪白的菜帮,鹅黄色的菜心,还有那随风飘荡夹杂着泥土的芳香……一下子就勾起我对大白菜的怀念。
窗前的林梢渐渐染黄,屋后的青纱帐变成了黄红衫,也正是北洼子那片大白菜疯长的时节。我不止一次地仰着脸问妈妈,啥时候生产队砍白菜呀,妈妈就会不厌其烦地对我说,别着急,车辘轱响萝卜白菜还长呢。盼着生产队砍白菜,其实我就是盼着妈妈给我们做大白菜、豆腐和粉条做馅的玉米面菜团子。
村口的铜钟响了,土街上传来了分白菜的吆喝声。父亲推起手推车,我和妈妈急忙跟在身后,随着大伙一边聊天儿,一边向北洼子白菜地赶去。赶上白菜地头时,生产队长正张罗着抓阄,父亲的手气挺好,抓到了长势很好的两条垄大白菜。妈妈并没有像大娘婶子那样,把白菜削得葱白一样干净利落。妈妈还不时地朝我和父亲嚷着让我们手脚轻点,别把白菜帮碰掉。妈妈把拔起的大白菜规矩地摆在手推车上,父亲临推走时,妈妈还会用细绳子把大白菜拢好,不止一次地嘱咐父亲把大白菜摆在仓房的屋顶,害怕让猪羊把白菜给糟蹋了。妈妈回到家里,挑出那些棵大又包得壮实的大白菜整齐地摆在仓房的屋檐上,每天还不止一次地翻动着,妈妈说把大白菜帮晒蔫点,贮存在土豆窖里,就是吃到春节也没啥问题。妈妈把长得散一些的大白菜收拾干净渍了酸菜,就是连拿不上手的小白菜,妈妈也把它们收拾起来,晒蔫后,编成了辫子,妈妈说等到冬天没菜的时候,还可以淖一下蘸酱下饭呢。家里有了大白菜,妈妈抽点时间就给我们做菜团子,多半都是玉米面,有时还会做土豆磨糊面,却很少做白面和粉面子皮的菜团子,馅却都是一样的,就是以大白菜为主,零星的豆腐和粉条,更不用说肉和油啦,就是这样,我们也吃得甜嘴巴舌,直到吃不下为止。
记忆中,村里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先是春天掐脖旱,五月份闹虫灾,七月份又发了洪水……别说收成,就是连种点大白菜的机会都没有。每家都分到了救济粮,虽说饿不死人,却也难以填饱肚子,尤其是孩子多的家庭,更是捉襟见肘。身为生产队长的父亲,私自做主,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带着村民套上四挂大马车去700多公里的辽宁拉冻白菜。三天三夜,父亲带着装得满满四挂大马车的冻白菜回来啦,全村人都沸腾了,村里人度过了一个没有挨饿的冬天,父亲,还有去拉冻白菜的叔叔大爷冻伤了手脚,多年以后,每到阴天下雨,脚和手还奇痒难忍,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个深冬拉冻白菜的事儿。从那时起,大白菜是救命菜,就在我的心坎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刚进城那几年,每到秋菜上市的时候,我都与爱人挑来拣去地买上二三百斤大白菜。渍上大半缸酸菜,剩下的大白菜就放在走廊和窗台上,干豆腐炒白菜片、白菜炖粉条、冻豆腐炖粉条、醋溜白菜片、酱拌白菜丝……反正,冬天过去啦,大半缸酸菜,还有二百多斤大白菜竟然都吃完了。那个时候,喜欢吃大白菜是一回事,更主要的是除了大白菜,也真就买不起别的新鲜菜吃了。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过冬的大白菜买得越来越少。到了秋菜上市季节,看着油绿的白菜叶,雪白的菜帮,禁不住就要买上它三五十斤,放在门口。想得相当好,吃大白菜了就取,开始几天还吃几次,过不了几天就忘了,等到大白菜干透、烂掉,爱人收拾时,就向我唠叨起来。那时,看着喜人的大白菜,我的手就又痒了,免不了又要买上三五棵,不时地催着爱人做粉条炖白菜,还有白菜炖冻豆腐,每次爱人都放不少五花肉,可我再也没有吃到记忆中大白菜的香甜啦。还是儿子说得好,不是大白菜不好吃了,而是我的口味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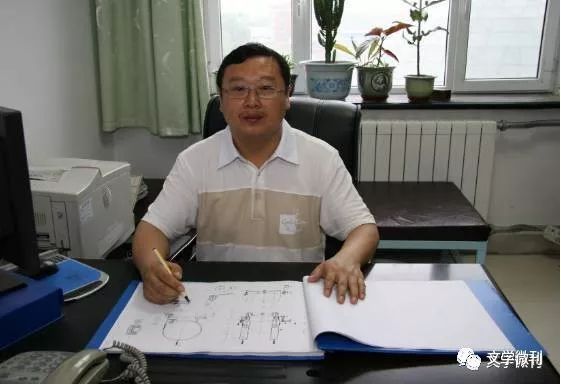

刘佩学,男,1967年9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300余万字各类文学作品发表,小说作品散见于《北方文学》、《北方作家》、《岁月》、《小小说选刊》、《地火》、《小说月刊》、《当代小说》、《天池小小说》、《检察日报》、《幽默与笑话》、《讽刺与幽默》、《文学故事报》等报刊杂志。

平台提取赞赏的20%作为平台运营,80%归作者所有。稿费以微信红包方式,10元以下不发放。稿件必须是原创首发。
请输入你的在线分享代码







额 本文暂时没人评论 来添加一个吧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