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总编辑、青年文学杂志社社长李师东,著名评论家作家学者孟繁华、陈福民、张楚、饶翔、傅逸尘、行超等出席研讨会。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围绕青年作家王凯发表在《青年文学》2017年第7期的中篇小说《沙漠里的叶绿素》,以及他近年创作的其他系列军旅小说, 就“军旅小说的新气象:从激昂塞上曲到血肉凡人歌;从王凯小说看当代军旅小说的新变化;和平年代的英雄主义应如何表达、新军人形象怎样塑造” 等相关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研讨会由青年文学杂志社执行主编张菁主持,《青年文学》编辑于亚敏、陈集益、赵志明全程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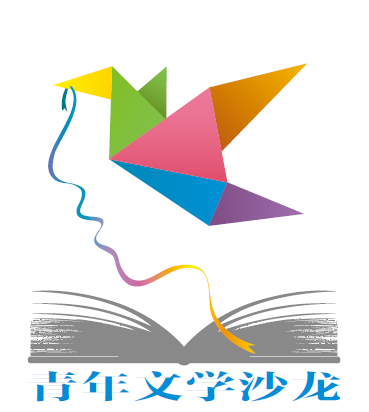

我一直关注王凯的创作。作为军旅文学的年轻小说家,文如其人。读他的小说和见他这个人都感到感到很亲切。《沙漠里的叶绿素》是军营小说,也是小题材。但后面有大背景,这就是军人的戍边生活。戍边的寂寞我们难以想象,于是谈恋爱就变得极具吸引力。通过几对年轻男女的恋爱折射出当下青年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毫无疑问受到世俗的影响,但又隐含了作者王凯理解的军人的价值观。军人的爱情和普通青年的爱情并没有区别,在王凯的笔下尤显真实生动,对男人之间的感情描写得非常精彩,对女性心理的拿捏稍欠火候。这几组男女的情感描写都很打动人心,军营里面没有多少故事,不比城市男女的复杂和多样性,军营很简单,因此更考验谋篇布局的深思熟虑,更需要小说的技巧。彭小伟这个人物此前不曾出现过,他对人对事的执拗、认真以及作家对这种执拗认真的表达,显示了王凯对人物的熟悉和塑造人物的能力。王凯小说的语言有戏谑的一面。这是自王朔始在青年作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小说叙事腔调。但如果使用的过多,这种叙述腔调的有效性将受到质疑。我认为现在已经难以为继。从王朔带来的小说语言、语调,开启了新京味小说,后面出现了很多小说家。总的来说,在小说创作中,写正面形象难,写二流子容易。但诚如柏拉图说:难的才是美的。王凯的小说主要写巴丹吉林这块不毛之地,但在不毛之地上,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文学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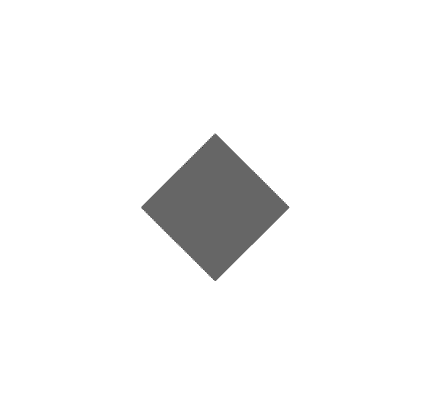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的题材划分,曾有其合理性,现在则值得商榷了。比如刚才孟繁华提出的军事文学的提法不太科学,在国外都称为战争小说。先把争议搁置一边,毕竟今天的主题是讨论王凯的小说。在我看来,王凯小说的题材依然是特定的。军人首先是成人,必须尊重成人(爱情)这个领域,必须捍卫这个领域。戍边的生活方式(以及创作方式)在中国文学中是有传统也有传承的,这也决定了不能把国家形制的军人职业与军人的个人生活截然分开来看。小说的题目:沙漠里的叶绿素,沙漠是苍黄的,叶绿素是绿的,黄和绿的对比非常有意思。此绿色是战士的青春和血液铸就的。小说有戏谑的一面,但背后是军人的职业献身精神以及良好的品质内核,是借修辞上的调侃表达尊敬。王凯延续了军事文学的传统,在新形势下又有了新的表达。50年代到80年代的军事文学的传统在90年代中期一度衰微甚至中断,对中国的军人及其军营生活都是一种不公平。王凯的军事小说,其意义在于,把被甩出去被无视的生活,通过他的笔触,使之重回视野。
《沙漠里的叶绿素》,其支撑点是“爱”,这点特别好。很大方,很光明正大。要知道,这个时代所有的世俗元素,军营都很难不受影响,但王凯的写作表明,他没有让世俗、市井之爱吞噬掉军人的自我,同时又始终以爱为支撑去丰富军人的内涵,这是很负责也很了不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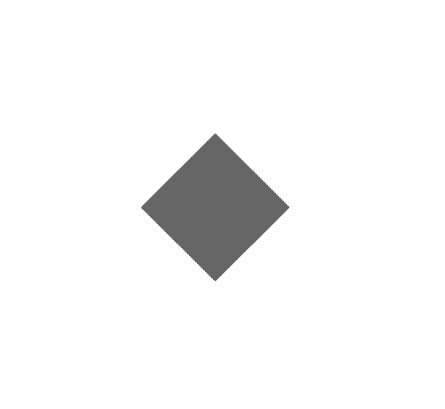

我想强调一下差异性。王凯的这篇小说《沙漠里的叶绿素》,体现了70后叙事的不同。与以往的军旅作品相比,小说明显带入了70后的成长信息。小说里的三个人物都有各自的爱情遭遇,他们在入伍前和社会上的年轻男女是一样的,但进入军营后就发生了变异,产生了断裂,和以前的生活告别是难免的。这些沙漠中的军人,内心的复杂性,选择上的多样性,增加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戏剧性。在军营这个特定场域,如何塑造自己,就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所以,我说《沙漠里的叶绿素》好就好在塑造了彭小伟这样一个人物。这个人具有技术型、专业型的职业特征,执着、耿直、认真,不圆滑,不世故,相信爱情。这种坚持体现了作者的思考,既是职业所系,也是价值所在。
在这里我也要提一点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小说的气象和格局还可以更开阔些。现在的小说在量上很多,但被公认的好作品越来越少。这也是我对70后、80后小说家的期望:多写好作品,争取写精品。尤其是像王凯这些比较成熟的作家,应该把精力放在人物的经营塑造上,人物要有琢磨、要有推进、要有逻辑、要有耐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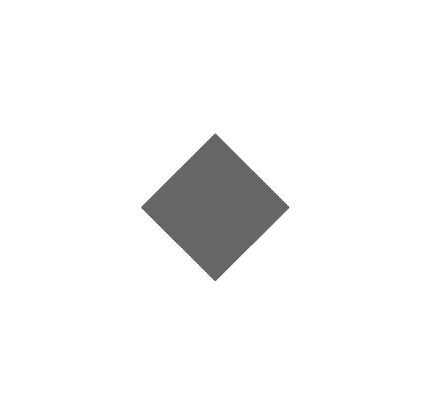

认识王凯始于2011年我们一块上鲁院的高研班。第一次读他的小说《沉默的中士》,我就被感动了。时隔6年之后,当我重读时依然被打动。好的小说能抵御时光的侵蚀。我想这部小说之所以如此动人,是因为王凯在写作时注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其实,在小说中注入作者的真情实感是件危险的事,因为一不小心,那些过于饱满的情绪表达会使小说变得浅薄甚至庸俗。但是王凯在叙述过程中极为精准地把握住了人物的情绪宣泄,不满也不溢出。这篇小说写的是部队里的兄弟情,写一个浑身流动着旺盛荷尔蒙的年轻指导员“我”,如何与他的士兵相处。小说里有很多特别真实的细节描写,比如中士张建军得了阑尾炎,指导员“我”把他送到医院,在手术单的家属签名栏里写下自己的名字时,忽然担心张建军会在今晚死掉,觉得内疚又伤感。“我”离开车站去政治部工作,跟张建军告别时,张建军说要是有仗打就好了,我想去打仗,我想跟着你出生入死。在这种双方渐进性的接触和了解中,部队中那种森严的等级制度造成的虚假的尊重和服从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是兄弟般的互爱与疼惜。
其实在生活中,王凯跟石一枫很像,爱讲黄段子和笑话。但是阅读他们的小说时,有种惊人的相似,那就是他们对生活真相的尊重和对人性中高贵美好的崇敬、赞美,或者说在他们的小说里,我才发现了他们的纯真、纯情、厚道和仁义。《沙漠里的叶绿素》是篇爱情小说,相对于《沉默的中士》等小说,王凯的笔调更为幽默俏皮,三个军中男人的恋爱史一波三折。“我”的成熟机智、何勇的市侩庸俗和彭小伟的执着坦诚,既相辅相成又独立发展。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彭小伟,貌不惊人的他是一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的人生准则中,爱情仍然保持着它的神秘、高贵与纯净,如果说与麦青青的恋爱是青春期的萌动,那么与风亦柔的恋爱则是成熟后的苦涩难言。理想与现实的错位让爱情也变得模糊。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面对生活时结局往往是挫败与逃离,但彭小军以自己的方式和姿势固守着内心的城堡,不让它被现实震得坍塌和分崩离析。饶翔在《青年文学》的同期评论中说,这种错位被美学化为一种堂吉诃德似的“不合时宜”的人物形象。确实如此。
王凯写沙漠,写军人,写爱情与友谊。军旅题材,向来是在针尖上跳舞或者戴着手铐跳舞。可我们在王凯的小说里,只感受到了他美妙的舞姿和笔下人物的真实灵动。这些人或挣扎或迷惘,或甜蜜或痛苦,可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姿势:那就是永远是在往前行走的路上。孟繁华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当下写作中普遍存在“情义的缺失”问题,这种缺失在王凯的一些小说里得到了显现,他含蓄地张扬了“情义的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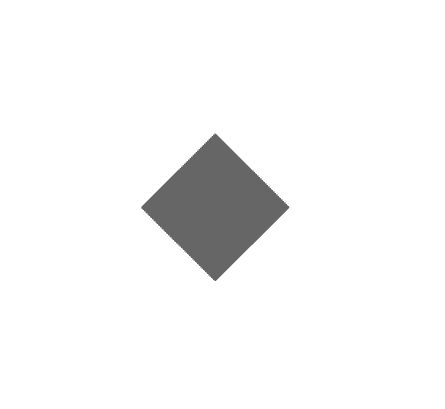

在我的印象中,王凯是一个诚恳低调的人。在青年作家中,他是不那么“热闹的”一个。他近期出版了小说集《沉默的中士》,也几乎没有什么动静,没做什么宣传。
作为一名年轻的军队作家,王凯的小说表现出“阳气很旺”的一面,他的《沉默的中士》《终将远去》都是纯粹的“男人戏”,他对军队这个环境中男人之间的“兄弟情”把握得很深入。这种感情有些类似于《水浒传》中男人们之间的感情,类似带头大哥与小兄弟之间的感情,这样的“男人戏”“兄弟情”属于“纯直男”系,可能会令女性读者不适,但是正如张楚所说的有“浩然之气”,如张菁所说的“有深情”,在粗鲁中也有温柔细腻的一面,坦荡纯粹而无功利,所以很动人。
王凯的小说很多带有“悲剧”性质,像《沉默的中士》《终将远去》。作者从正面去处理悲剧,这样的悲剧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悲剧——人物为了维护他所坚持的价值,不惜与命运、与所处的现实环境相抗争,却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这样的悲剧从叙事语言到审美意蕴都给读者以崇高感。
但是在《铁椅子》和《沙漠里的叶绿素》中,我能明显感觉到作者叙事语言的改变,他的语言很戏谑,很有快感,人物则有一种怪异和荒诞感。我以为王凯在此经营的是一种“后悲剧”。他大概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后理想主义”时代,我想纵然他仍心怀着残存的理想主义信念,恐怕也难以再用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达。故而,他以一种滑稽戏谑的叙事语调,写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写出了“理想主义”在“现实主义”时代所遭遇到的种种尴尬。这使得小说具有某种戏剧性和喜剧性。然而,《沙漠里的叶绿素》结尾,当彭小伟举起他为了向丰亦柔证明其爱情忠贞而自伤的手指头,反问“我”:“你能说,这不算爱情吗?”这凛然的发问,却真让我们无言以对,悲从中来。
《铁椅子》和《沙漠里的叶绿素》写的都是与时代有错位感的、堂吉诃德式的不合时宜的人——他怀抱理想却脱离现实、耽于幻想,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这使他的行动看上去滑稽而夸张;然而,他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他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令我们折服。这让我想起阿甘本对于“同时代人”的理解,“同时代人”并不是与时代完全保持一致,而是与时代有距离的人,这种距离感使他更全面深刻地把握这个时代。从王凯的这些小说中,我感觉到了他的“同时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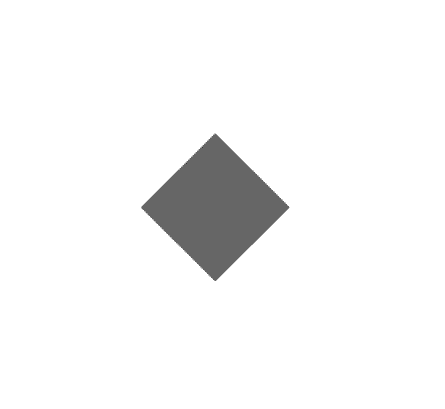

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代表,王凯有着扎实完整的部队任职履历,基层与机关生活体验丰厚而深切。他善于挖掘表现日常生活中人物丰富的生命情态和驳杂的心灵世界,对年轻一代官兵在军营与社会的急速变化中面临的各种尴尬的精神处境和命运遭际进行了富于生命痛感和思辨意味的追问与批判。王凯颠覆了传统军旅小说的宏大叙事,凸显了带有英雄主义情结的主人公在现实面前不断妥协,理想和伦理道德两相冲突的困境,表现出作家对昆德拉式“存在”的焦虑。
王凯的小说具有一种挽歌气质。世俗化的关系与军营战友情的冲突、错位,欲望失落与无奈忧伤是王凯小说的常见主题。当所有人都无力自拔的时候,人的灵魂、命运和现实生活之间形成了悖论,这悖论里堆积出荒诞感,于是小说便开始接近寓言。在意蕴上如此尖利冲撞的主题,显然源于王凯对世界的冷眼和质疑。王凯的叙述看似漫不经心,内在气质里却有着深重粘稠的质疑和悲悯,是那种深植于大漠的粗犷和苍凉。王凯就像一个手工匠人,拿着放大镜捕捉着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某座军营里一群年轻官兵的喜怒哀乐。
灰蓝色的沙漠,暗绿色的军营,荒芜恶劣的自然环境,体制内部的现实压力,对那些年轻军人的宝贵青春而言,无疑构成了压迫性的“存在”。面对那些硕大无朋而又坚硬无比的“存在”,青春、理想、欲望、爱情的柔软肉身遵从着心灵的召唤,在狭窄逼仄的空间里横冲直撞,遍体鳞伤。王凯的叙事细腻绵密,严格地遵循着生活本身的逻辑,可延伸到最后,往往得出的却是与世俗和现实背道而驰的结论。这正是王凯的高明之处,他的视角是独特的、异质性的,对现实和生命都怀揣着强烈的质疑和焦虑。他笔下的人物大都外表平静、内心执拗,执着探寻和追逐的是不同于世俗逻辑的另外一重可能性,是精神的飞升和超越,是人心的不同选择。王凯擅长记叙一个生命的截面、一个静态的特写、一种氤氲着复杂情绪的场景,但是读后那一种或灿烂或黯淡或悲壮的生命情状,却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带有某种哲学思辨的意味。
在我印象中,王凯没有直接描写过战争,他塑造的多是和平环境下的职业军人形象,且主要写的是“小人物”。精神上的漂泊和焦虑,在王凯的军旅现实题材小说中有较多投射。传统军旅文学中那种单纯的“崇高感”则被他幽默调侃的语言解构掉了,小人物琐细庸常日常经验被置于前景,凸显、夸张、放大。这种日常化、碎片化、低视点的叙事伦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它局限了作家的视野,阻碍了作家的想象力。因此,题材的重复、叙事的模式化以及想象力的相对孱弱,或许是制约王凯超越自身经验、建构更为广阔的文学空间、向着更加优秀的文学之境深潜的核心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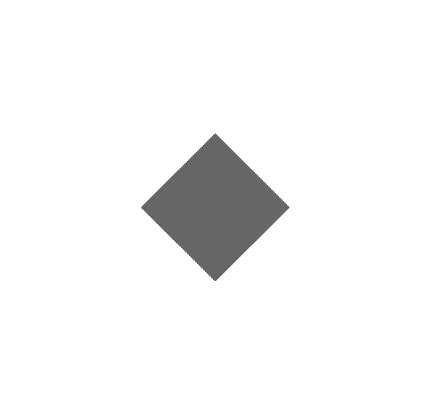

王凯的小说有一种庄重感和庄严感,在我看来这应该是好的军旅小说必备的特点。但王凯小说的庄重、庄严并非来自其主题和内容的宏大性,事实上,他的小说写的常常是军营里最平凡、最不起眼的人,甚至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然而正是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久违的“崇高”。我想,这样的精神气质其实是源自写作者对军人、对军旅生活以及对于人和生活本身的体恤和敬意。
王凯的小说有“冷”的一面,《沉默的中士》《终将远去》等作品在情感表达、叙述语气等方面都非常节制,具有类似巴别尔、海明威等人的小说那种“纯”与““正”的气息。但与此同时,王凯小说的底色却无疑是暖的,他以巨大的善意和耐心对待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正是在这种冷暖对峙中,王凯成功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多面性、复杂性,同时又不失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 “典型人物”。
虽然王凯的小说写的都是军旅生活,但是如果用“军旅文学”来概括他的创作,我以为对他是一种局限。他的小说的确反映了当下军旅现实和当代军人的生活,但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此。“军旅”与“官场”、“职场”、“校园”等类似,只是人的一种处境。在这种特殊的处境中,王凯发现了人性深处的、本质性的问题。比如,王凯的多篇小说都涉及退伍、转业等问题,但他并不仅是呈现这个现实问题,而是书写一种“离别”——人是怎样一步步制造了离别,又是怎样面对离别,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的复杂多变与难以捉摸。而这一主题,恰恰是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一直在面对的问题。
王凯笔下的“兄弟情”很动人,这种动人并不是煽情的、眼泪汪汪的,而是具有一种“直男”的钝感和痛感。与之相比,王凯笔下的爱情却显得脸谱化和概念化。他似乎一直在书写一种女人——始乱终弃的女人,也一直在书写一种爱情——单相思的爱情。作为一个女性读者,我期待王凯在今后的写作中,将他对自己笔下男性人物的惺惺相惜或同情之理解,也分享给他笔下的女性人物。
请输入你的在线分享代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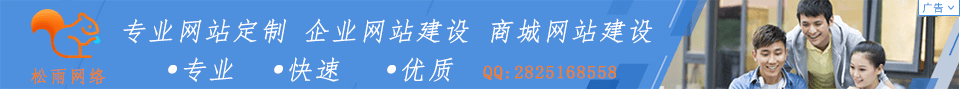



额 本文暂时没人评论 来添加一个吧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