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上一篇: 十万个冷笑线章隐藏任务完成攻略
- 下一篇: 薛立兴:满目金黄银杏叶(散文随笔
参考消息网10月13日报道 今年9月,美国电视剧集《使女的故事》在第69届黄金时段艾美奖上包揽最佳剧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最佳导演等诸多奖项。艾美奖是美国电视界的最高殊荣,黄金时段(泛指晚间时段)“剧情类最佳剧集”是分量最重的奖项之一。
《使女的故事》根据1985年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同名经典反乌托邦小说改编。故事发生在2020年至2030年间,袭击华盛顿后,美国的基督教激进分子夺取政权,建立了极权国家——基列共和国。这也是一个男权社会,女人受到严格控制,无法拥有财产。她们依照功能被分成不同等级,授予不同的工作,例如,夫人、嬷嬷、玛莎、使女、妓女等。

这部刚柔并济的电视剧回应美国当下社会全面保守化的现实,却也警醒了全世界。此剧将生态恶化导致的人类人口危机、清教传统下的一夫一妻核心家庭禁欲-生殖伦理观,以及代议制民主进程对宗教极权国家这一(可能的)最终命运无力抵抗和恐惧等刻画得淋漓尽致。
该剧的观赏性还体现在表现手法上,它力图将“极权制度对个人身体/身份规训”这一严肃话题化解为随角色遭遇而嬗变的个人化体验。该剧结构双线交叉汇合:叙事从头到尾由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不间断展开,主线为按时间顺序发展的“此刻”,副线为此刻事件引发的各种非线性“记忆片段”或者交代情节的闪回,各个片段之间相对独立。
主线的情节沿着基列国家庭内部大统领弗雷德家的“受孕仪式”和外交“使女贸易”为核心的奴役与反奴役行动逐渐演进。同时,全剧关键角色“使女”奥弗雷德(本名“琼”被禁止使用,奥弗雷德的英文名可以拆开,意为“属于弗雷德”)在主线中的生活围绕着两个表面上各自封闭的社交圈展开:其一是冷寂如同地下室的“特权家庭沃特福德”,其二是使女们被召集参与行刑的“救赎广场”和买菜的“采购市场”。在沃特福德家中,奥弗雷德唯一合法作用是提供生育服务,用她自己的话形容是“两条腿的子宫”,而奥弗雷德和外界的联系,都需要通过比她高级的“家庭成员”来实现。

宗教作为一种日常,规划丈量剧中每个人的方方面面,包括最为琐碎的打招呼:无论何时何人之间,见面问好都要使用一套全新的、严格的敬神句式。但是神圣家庭的夫妻却生不出孩子,于是通过给生育能力完好的失足妇女“定罪”,以便后者主动供奉自己的身体来得到“救赎”。大统领沃特福德夫妇间的生育职责被实质性地嫁接到使女身上,妻子们装模作样分娩阵痛的样子,简直令人做噩梦!
可以说,政教合一的基列国与其说供奉的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不如说供奉的是具有神圣生育义务的基督教核心家庭。在异性婚姻制度濒临瓦解、环境污染导致普遍无法正常生殖的大环境下,基列国以“亡国灭种”为鞭策,炮制出重建基督教核心家庭伦理的施政纲领,呼吁美国人重建神的国度,将人降格为商品的同时,把制度优越性一并输出到国境之南的墨西哥。
女主角使女奥弗雷德每一天都由他人精确安排,严禁单独行动,于是体现个体自由的时刻,除了间或出现的“密谋造反”情节,便是和“此刻”高度关联的“记忆片段”(也即副线)。这也是整个片子集中用私密性来构建艺术性的部分,通过改变画面焦点、精确的交叉剪辑和环境音画外音效延伸等手段,很好地让观众进入到角色“时而哀愁、时而绝望、时而恐惧、时而振奋”的情绪中。
虽然在表现其他使女时多采用第三者视角,但丝毫不减其影像的残忍冷酷。 无论是主线还是副线,该剧大量使用精确的配色,第一人称视角,广角镜头浅景深突出角色面部微表情等方式,来让私人体验更为可感,同时也反复让观众知道这些情绪其他角色是看不见的。整部剧集的结构如同一种囚室套着另一种囚室, 令人不忍多看又忍不住不看,不忍回想又不得不回味。

作为能成功的政教合一极权,基列国用政变的手段将“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实体中貌似式微的父权制内核提炼而出。众所周知的是,宗教父权制对群体身份和个人身体的规训是不分阶层或男女的,这在剧集中皆有角色化的体现。
在剧中,如司机尼克一样的低阶层,需要为国保持单身才能达到忠诚的及格线。感情和性需求无条件服从管理。在对不同家庭命运的处置上,我们也能看到该剧着力于揭露宗教父权意识形态下无差别的压迫属性,以及由其派生的制度性虚伪和个体“男子气概”的无力。父权制也往往建立在普遍的双重标准之上——和卢克因不良记录痛失妻女相比,大统领弗雷德·沃特福德不仅有“贤妻”相伴,还有法定的代孕使女和地下俱乐部的玩物——权力在此,宗教戒律似乎纷纷网开一面。
但是,别以为等级森严和“弱肉强食”是对广大男性的激励;不幸的制度可以让任何人不幸:主教沃特福德可享用三个女人,但次次徒劳无果的播种仪式却严重制约了他在官僚系统中的合法性。当病态制度让“子嗣”成为一种政治资源时,至亲也能以善的名义作恶。两人由以往纯粹的“革命爱情”逐渐割裂嬗变为貌合神离、互相利用的组合。该剧似乎还带着一丝恶趣味地讽刺了传统性别分工:两人密谋政变时,弗雷德为妻子塞雷娜在政坛纵横捭阖的形象所着迷。建国后弗雷德官位扶摇直上,而塞雷娜成了笼子里的金丝雀,他却再也无法对她提起兴趣。压抑的家庭生活让弗雷德的欲望变得扭曲,使他热衷于一边把使女豢养成玩物,一边对其进行道德说教。而塞雷娜抱持“让女性回归家庭”的主张出尽政治风头,到头来一路都在自掘坟墓,只剩“子嗣”这一个途径玩弄权术——以至于塞雷娜丧失人性地以奥弗雷德女儿汉娜的性命要挟她。
该剧力图通过影像再现宗教父权制下的种种体验,即便如此,也只不过将此时此刻在世界各处实际存在的制度化性别暴力,在时间地点中高度集中在了“前美利坚”的土地上,从而产生爆炸性的戏剧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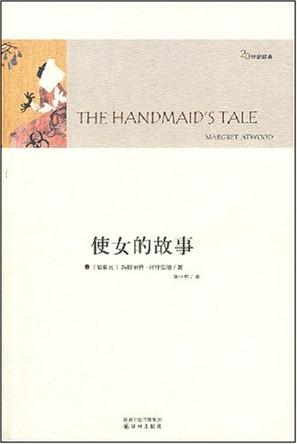
今年5月,《使女的故事》原著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她在去年美国大选时,听到一些共和党人说“如果女人怀孕了就不能说是强奸”,这让她感到和她的小说中所描述的何其相似。“一夜醒来,她们发现自己不再是在看幻想小说”。她希望电视剧《使女的故事》,能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的危险。
作为一个显然的内政电视剧,《使女的故事》只是激发各种动员行动中一个“活色生香”的火星,真正的火星恐怕还是——美国当下政治场域上经济恢复乏力的状况下,女性权益斗争的节节败退。譬如,最近半年以得克萨斯州为代表的传统地区,反堕胎法案和“一刀切”的反公立医保提案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生不起又不让堕,意外早孕的单亲妈妈们处境极为困难。
或许,这部剧难能可贵之处,其一便是将性别平权运动背后的自由解放平等价值,以及其渐进发展的历史观抖搂出来放在桌面上进行审视。也就是说“美国人也可以一夜回到解放前”这种提醒批判了发展主义的人类史观——自由平等是未来、压迫和剥削终将只属于过去。同时,该剧对父权派生内因的推断过于天真。核危机、性解放、妇女平权和避孕药一起构成了生殖危机和末世情绪,继而给宗教父权的复辟提供了广大的群众基础——仅此而已吗?似乎需要比尔·克林顿跳到片场大喊:“笨蛋,问题是经济!”
但是,第一季经济形态刻画的明显缺位反而能促使人们发现当下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和对“发展主导”话语的反思:以人口理论为核心的“生存危机”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前提,以维持人这种高等生物的有效代际更替是本剧未言明的父权内在逻辑,那么下一步是什么?粗略地说,这是一个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也是一个“攻城略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至今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一部优秀电视剧所提出的警示之所以有效,更在于它充分地提供了设身处地感受“无孔不入的压迫”情境来激发观众去思考作为或不作为的后果。剧集中的种种暴行每天都在地球另一角落发生,因为不是切肤之痛而无法关心,或者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无法将关心落到实处。那么,该剧并不是要它的目标观众立刻组织起来寻求途径解放这些十万八千里外的人,或者再造一个新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影视界择机改编经典文学也是一种颇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作为1980年代出版的小说,《使女的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一种制度性复古的未来设定在今天,也恰恰是在今天的“前美利坚”,基督教神治主义军事管治下的日常恐怖以写实的影像风格搬上了网络与荧幕。这显然是一种双重的借古讽今。但该剧表现的不仅仅是特朗普时代女性权益的“全面倒退”。需要重现审视的是这种“倒退”依然带着美国“自由主义”一丝精耕细作一亩三分地的侥幸。(此段加粗)
与其说该剧影射的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面复古,不如说是在想当然的现代性表象之下,美国土壤上根深蒂固的仍是清教徒意识。无论是书中基列共和国起事的马塞诸塞州剑桥,绞刑示众所在的哈佛大学院墙,还是电视剧女主一家生活的波士顿,都是当下美式“自由主义”思想的发源地,无疑都是美国人一眼即可感知的警示。
好在文艺作品、创作者以及观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互生的,普遍性和独特性在这些关系中交织产生新的意义,且并无定律。这提醒我们对《使女的故事》保持开放态度,任何地方的人都能从该剧中有所得。
在特朗普上台前,妇女们的抗议便已年年有,但是今年3月在得克萨斯反堕胎法的抗议中身穿使女红罩袍,头戴白遮挡,着实吸了一把睛。使女的着装是一种“梗”,正如在另类右翼扎堆的布赖特巴特流行起来的绿色悲伤青蛙,也正如剧集中的那串本属于大统领沃特福德童年记忆的拉丁文暗语,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滋生出新的话语力量。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请输入你的在线分享代码







额 本文暂时没人评论 来添加一个吧
发表评论